發送翻譯請求時,我附上了「請務必先遊玩後再開始翻譯」的遊戲版本。
取自文本
結果兩天後,我收到了相同內容的回覆:
“我真的是哭了”。
當時還沒有音樂的情況。
今年1月,韓國的獨立開發者SOMI發布的新作《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在Steam上創下了5000多條的壓倒性好評評價,引起了熱烈討論。遊戲的系統、音效及故事均獲得高度評價,許多評論中出現了「感動」「共鳴」「療癒」等共同表達。
在韓國釜山從事法律界近20年的SOMI,過去十年來以《REPLICA》《LEGAL DUNGEON》《The Wake》為首,發表了6部作品。以主題傳遞社會信息引起關注的他,這次表示希望能創造出「完全與自己分離的世界」,在享受《未解決事件》的玩家之間引起了巨大關注。
今天,SKOOTA專訪了超越韓國、在全球備受矚目的獨立創作者SOMI本人。希望能生動地傳達他在創作過程中的秘辛及其背後的思考,這些是所有玩過他遊戲的玩家所渴望了解的內容。

SOMI(ソミ)
2014年以《RABBIT HOLE 3D》正式出道
代表作:《REPLICA》(2016)、《LEGAL DUNGEON》(2018)、《The Wake》(2020)
最新作:《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2024)
2016年 INDIE STREAM Festival 獲獎
2020年 Indie Arena Booth 最佳敘事遊戲獎
2024年 A MAZE./Berlin 2024 大獎 及 BitSummit Drift 遊戲・設計最優秀獎 BIC Fest 2024 評審委員獎、社會影響獎等多項獲獎經歷
目前,在法律界工作,同時作為獨立開發者持續創作
20年目の法曹、かつ10年目のゲーム開発者SOMI「偶然と好奇心から始まったゲーム開発」
――最近,受到韓國以及日本廣泛討論的獨立遊戲界知名開發者SOMI,歡迎您。能請您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嗎?
SOMI: 首先「有名」這個詞對我來說並不合適(笑)。我是韓國釜山獨自一人緊張地製作獨立遊戲已近10年的SOMI。2014年發佈了《RABBIT HOLE 3D》後,目前已發布6部作品。代表作有構成了罪惡感三部曲的《REPLICA》(2016)《LEGAL DUNGEON》(2019)《THE WAKE》(2020)。而在今年1月以《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2024)為標題發布了最新作,正在全力以赴進行宣傳活動。
――聽說您並不是全職開發者,而是將本業與獨立開發並行進行。您提到已經進入遊戲製作10年,您在進入遊戲開發之前,是從事何種創意活動的呢?
SOMI: 大學時期非常渴望成為小說家。我寫過短篇小說,參加文學比賽,真的很努力想要成為小說家。雖然因為能力不足無法正式出道…但是有這段經歷。在那之前,高中時期我非常想成為漫畫家,經常模仿漫畫畫畫。
――從想成為小說家或漫畫家到現在的遊戲開發,這段過程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呢?
SOMI: 基本上,我在大學時期主修法律,現在也在法律相關的職場工作。我已在當前的工作場所工作了20年,已經非常習慣了日常工作如同哈姆斯特的跑輪般的生活。在這期間,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創作活動,認為這或許能成為生活的活力。例如,能發泄內心的想法和壓力。於是我決定自學程式設計。我透過這個學會做應用,並發佈到應用商店。例如我做過一個用塔羅牌占卜的應用,或者有一個能在一年後發送信件的應用。類似這樣的東西。
――聽起來您似乎是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方向,而不單是一味地堅持某一件事情。那麼您是如何最終邁入遊戲開發的呢?
SOMI: 我曾經獨習程式設計並嘗試製作應用的同時,我在考慮下一部作品該做什麼的時候,看到當時在手機上非常受歡迎的遊戲《Super Hexagon》(2012)。那是一款非常精彩的獨立遊戲,但我當時對於獨立遊戲的理解還相當淺薄,我也不算是特別享受遊戲的人。因此即便我玩了這款遊戲,也無法認識到它的真正價值,當時我心中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稍微做做這個,我就能做得比它好」。於是就構想出了《RABBIT HOLE 3D》這款遊戲。
――如今的SOMI與《RABBIT HOLE 3D》的氛圍有著很大的差別呢(笑)。
SOMI: 其實我現在仍對節奏遊戲抱有強烈的熱情。當被問到「您接下來想做什麼作品呢?」時,我經常回答:我想做一款真正的音樂遊戲。還有,我非常喜歡Chiptune音樂,心中也有一個小小的目標,是想做一個能超越《Super Hexagon》的絕妙音樂遊戲。
――聽說您曾經製作過應用,看到在韓國的應用商店上名列第三,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應用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動力,這樣的情況下,您為何選擇進入遊戲開發呢?
SOMI: 我覺得這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其實我開始製作應用的契機也是非常偶然…雖然這個故事不適合現在談。從製作應用轉向遊戲開發,事實上是因為在思考「下一個應用要做什麼」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工時相對低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居然引起如此大的反響「那我也可以試試看…」,就是這樣的心態開始的。在這過程中,我也意識到「原來製作遊戲的過程難度真的很高,每一款看似簡單的遊戲背後,其實都是大量的研究和努力的成果」。
從形式到訊息「不要將政治引入遊戲」
――提到「好奇心」,我想詢問一個問題。您提到是因為好奇心而開始創作第一款遊戲,那麼在隨後的SOMI代表作「罪惡感三部曲」中又是什麼樣的好奇心呢?
SOMI: 在製作《RABBIT HOLE 3D》後,我之後又製作了一款名為《RETSNOM》(2015)的2D解謎遊戲。在這過程中,似乎逐漸找到了在2D遊戲中加入故事的方向,例如逐漸在像素藝術中嵌入小故事。隨著我想到要製作《REPLICA》*的時候,「在《RETSNOM》發佈之後,我在思考下一個遊戲要做什麼」時,我在某個地方遇到了一個在手機畫面上用像素藝術製作出的圖像。當我在網路上搜尋時發現了這個圖像,讓我不能自已,「是否有即以整個手機屏幕為場景的遊戲呢?」於是在那時,我發現這樣的遊戲根本不存在。因此我想,如果將這個畫面全都用像素藝術展示出來,那就會變得非常美麗,記得當時是從這樣的視角進入創作的。
也就是說,REPLICA這款遊戲是首先建立了形式。是因為想其中構建出手機屏幕,然後畫面上運行著聊天應用程序的過程,照片,和各種應用所組成的系統。這樣做之後,才開始逐步將故事加入進去。順便提一下,最初進入REPLICA中的故事與現在發佈的版本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故事。
*罪惡感三部曲的開端作品。
――可以說「REPLICA」作為罪惡感三部曲的起點是從形式開始的遊戲,這一點實在令人震驚。關於故事,之前提到的與現在完全不一樣,能否請您再詳細說明一下?
SOMI: 最初我打算基於1955年的小說《太陽的後裔》來創建故事。一位名叫湯姆的主角,殺死別人後過著他們的生活,他的劇情線是接近一位富豪的兒子迪基並殺了他,以至於自己仿佛變成了迪基。湯姆在殺死迪基之後,持有迪基的手機,試著對認為迪基還活著的迪基朋友說「如何製造出殺人事件沒有發生的理由」的故事。在構建著這樣的架構時,向朋友展示並進行遊戲測試的過程中,2016年發生的事件也發生了。您應該知道,當時韓國在朴槿惠總統的彈劾及彈劾要求的抗議中,社會上發生了非常大的事件。
SOMI: 在那之前,報導、出版、播報等方面的壓迫,以及各種黑名單事件也接連發生。在那個整體主義氛圍逐漸濃厚的時候,我逐漸感到羞愧,因為看到其他市民站出來反抗而自己卻什麼也沒有做。因此我也想有所作為,於是覺得透過這款遊戲講述這個故事或許很有意義。基於這個理由,我徹底改變了要放入的故事,這也成為了《REPLICA》的誕生,並且開啟了罪惡感三部曲的旅程。
――2016年這段時間,聽眾可能都能回憶起當年發生的重大事件,而這些事件對您創作的影響真的是令人驚訝。不過,在遊戲這種媒體中處理社會問題,尤其是當時反感會更為強烈,您當時真實的感受是什麼呢?
SOMI: 是的。當時透過遊戲討論社會問題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我從未見過有關政治問題及國內各社會問題的作品。實際上,在我年幼的時候曾經有過一些總統之間鬥爭的吐槽性遊戲,但此後幾乎未見有關社會問題的作品,或是攻擊性地處理社會問題的作品。推廣遊戲這一媒介的環境本身,我都覺得是將這個類型的範疇縮小的原因之一。
我想補充的是,「遊戲如果不有趣」或「遊戲必須帶來樂趣」的觀點過度強調,我衝擊了媒介的本質,在這種情況下削減了能夠實現的多樣性。最近流行逐漸有變化,其中原因也在於遊戲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確立為藝術類型之一,遊戲必須有趣的那種體制還在維持,這樣的趣味是因人而異的理解。也就是說,有些人會喜歡非常簡單的乒乓遊戲,而有些人則通過分析故事結構以及故事裡的人物關係體會非常巨大的快感…這正是認知上的差異。的確透過各種類型以及不同層次的人們正在享受各種不同的樂趣,這也使得一些年輕一代的人們意識到他們能夠以他們的獨立遊戲去接觸到各種群體,我認為這就是讓他們開始創作遊戲的原因之一。
此外,全球化的觀點也在改變,所謂的影響力遊戲與嚴肅遊戲等不同類型的遊戲也逐漸成為一個類型的眼光。同時針對這些遊戲所設立的獎項也漸漸出現,這類遊戲的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的確立,這方面對市場的看法也開始有所變化。基於這些理由,我覺得這種氛圍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
――您的觀察非常正確,我認為正是這種認知的變化支持著當下多元化的獨立遊戲。如果身處這樣的一個變革期,您覺得「不要將政治引入遊戲」這種聲音至今仍然存在嗎?
SOMI: 是的。在《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的評價中,有人提到「終究是因為想要做政治才製作的遊戲」。而且在韓國,圍繞著女性主義的各種問題出現的時期,我對於女性主義壓迫的思想檢查發表了強烈的立場,因此在遊戲玩家中成為了批評的目標。無論是在網路上,還是每次遊戲發布時,都能在未解決事件的相關討論區上看到明顯的兩種聲音。
一種是指「這是由女性主義開發者製作的遊戲,」「再也不想看,避免它」「絕對不會買」的視角。而另一種則是「這位開發者擁有正確的觀點,所以可以信任他的遊戲,安全地體驗。」簡單來說,現在有許多人非常忌諱在遊戲中表達個人觀點、立場、思想或哲學的傳遞。這是過去和現在我都在經歷的情況。
――在相關的訪談中,您提到非常感激「你是最好的女性主義者」的評價,這令我印象深刻(笑)。
SOMI: 我一直在努力去達到那樣的境界。因為還有很多要學的東西。
想要從遊戲中消除的正是「自己」 「我想創造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
――接下來想進入正題。《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與之前提到的罪惡感三部曲不同,您在訪談中提到「作為一款有面孔的遊戲來製作」,這裡的「有面孔的遊戲」是什麼意思呢?
SOMI: 之前的罪惡感三部曲沒有任何人物的插圖。通常在了解到人物、角色的過程中會閱讀台詞。透過這些台詞進行推理:「喔,這個角色大概長得這樣」、「年齡大約是這個樣子」等。在這當中,有一天,《LEGAL DUNGEON》的日文翻譯出現了相當糟糕的情況發佈出去了。雖然這樣的翻譯,仍然讓製作《Gnosia》(2019)的Petit Depotto,的伍悲珍及小貓兩位非常喜歡這部作品。
於是他們與我聯繫,即使是在即將發售的《Gnosia》前,仍然從頭到尾徹底修正了翻譯,並且還幫我畫了插圖。最終這插圖伴隨著Switch版本發售時,人們的反應與之前完全不同。實際上與《法律地牢》的早期版本相比,只有插圖一張的區別。翻譯的問題在Switch版發佈之前就已經解決,所以,透過這張插圖人們對這個角色的感受完全不同。當時我有點意識到這一點,雙方對這張插圖的想像限制的觀點,可能同時也是讓人們感受到角色活著的由來。
――聽說《Gnosia》最近決定動畫化。
SOMI: 沒錯,這真的很棒。
――那麼,是否可以期待有朝一日SOMI先生的作品也能動畫化呢?
SOMI: 若真的這樣那實在太榮幸了。能夠看到像《LEGAL DUNGEON》這樣的作品被製作成動畫或電影,我想再沒有比這更榮幸的事了。
――您在剛才的回答中提到「插圖的存在可能會限制人們的想像力」,是不是在《法律地牢》之前對插圖有過一些負面印象呢?
SOMI: 並不是特別的負面看法。製作《REPLICA》《LEGAL DUNGEON》時,我始終抱有一種想法是希望能進一步引導使用者對作品最合適的想像。例如…
嗯,其實《REPLICA》是我認為不需要人物的遊戲。透過強調對人物的抽象性,我想去表達出這是一個任何人都能經歷的情況。或者更鮮明地表現出囚徒困境的狀態,或者在這款遊戲中更關心手機功能的部分。至於《LEGAL DUNGEON》,則在對話場景中,階級標誌被用來替換人物。強調人們並不被視為個人,而只是作為其中一個齒輪的功能。還有,《LEGAL DUNGEON》中,主角的性別幾乎也不會出現,在結尾之前都不會知道性別,因此這樣的模棱兩可,可能也試圖帶給人們不受限制的想像力。
――明白了。透過小貓小姐的插圖使我發現作品的新視角,而在《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中,您以前想創造有面孔的角色。這樣的思維在實際製作中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SOMI: 創造有面孔的角色不僅特徵鮮明,也成為了後續得知的部分。在製作遊戲完畢後,我終於意識到「喔,這裡有這樣的區別」。不同於先前提到的罪惡感三部曲,《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是先製作內容的。對比我在製作《REPLICA》《LEGAL DUNGEON》《THE WAKE》時,並不是先構建形式,而是把故事寫完整,思考如何最有效地展現這個故事,進而形成形式。在故事的創作過程中,自然而然更需集中於這個角色的樣貌。
――與您之前的作品不同,須先完成故事這一點,能請您再過問一下嗎?在之前的訪談中,您提到「遊戲中的訊息很重要,但在此之前,遊戲應該要比訊息美麗,同時也必須變得重要」,能否進一步解釋這句話的含義呢?
SOMI: 我在這方面並沒有完美的哲學。不過,我在製作罪惡感三部曲的過程中會感覺到自己不斷被削減。也就是說,當時我所感受到的罪惡感,我想要改變的社會部分,還有像「你們是否也有相同的感受」「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會怎麼做?」這樣的情緒。利用遊戲這一媒介來徹底表達這種情緒的方面,其實在製作《THE WAKE》的時候感受得特別深刻。
SOMI: 這款遊戲完全是我自身的故事,因此遊戲製作成為我排解創傷和根深蒂固的壓力的過程。不過,這也讓我覺得,遊戲過於依賴於作家的經驗,因此當我在考慮製作下一款遊戲時,希望能夠創造出「完全的創作物」。也就是「我想真正的創造一個虛構的世界」。這樣一來,出現的人物也將與我毫無關聯,這些角色中的情節及由此產生的情感將完全與我在社會或生活中獲得的經驗無關。我想要創造一個完全陌生的空間,因此若SOMI這個人消失,作品依然會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存在。我內心懷有這樣的抽象思想,想要首次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
是的,我期望能在思想中同時探討主題的完美與美麗世界。因此對於遊戲的接觸及其主題思考,一部分是針對我對於遊戲的過去觀念的反作用。因此,遊戲應當如此的命題,與其說這樣倒不如說,我過去是基於既有的想法製作遊戲,因此這次或許僕可以嘗試一些新的氛圍的遊戲,這樣的想法。
――您提到希望描繪出一個不需要自己的世界,而這正是「充滿溫暖的愛與人性之美的世界」,這讓我感到複雜又些許寂寞。透過這樣的世界,讓所有人都感動、心靈溫暖,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啟示,不是嗎?
SOMI: 有些寂寞(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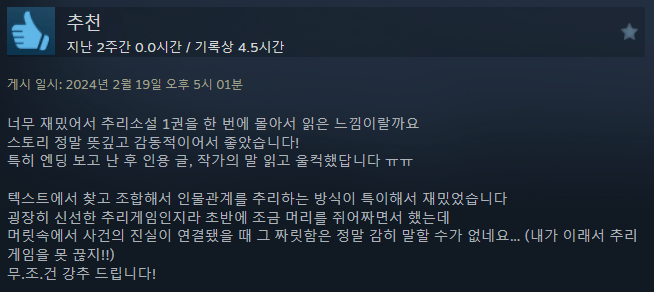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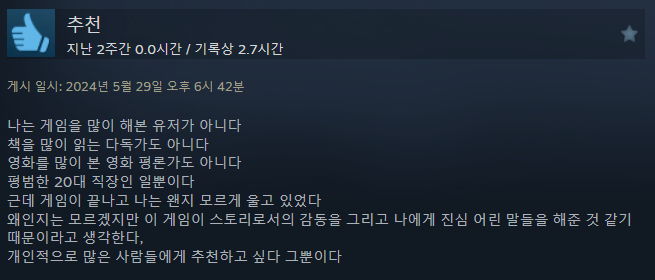
――在發布之前,您是否預測到自己的作品會受到如此多人的讚譽與共鳴?還是感到完全意外呢?
SOMI: 在這方面,我同時感受到「預期」與「未預見」的矛盾感。一般來說,在發佈前的情感波動十分大。有時候會覺得「這完全是個大熱門遊戲吧?」而有時卻又覺得「誰會玩這麼無聊的遊戲?」如此複雜的想法不斷交織。當我把遊戲發送給開發者不久,朋友和發行商們的反應卻很平淡。因此我就心裡想「這次又做了一款只滿足自己欲求的遊戲」。然而在之後,我試圖將這款遊戲本地化,於是將遊戲發送給翻譯者。最初我打算包括英語、日語和中文一同發佈。發送翻譯請求時,我附上了「請務必先遊玩後再開始翻譯」的遊戲版本。結果兩天後,我收到了相同內容的回覆:“我真的是哭了”。當時還沒有音樂的情況。翻譯同時進行音樂製作的時期,看到這封郵件我有種感覺,「Ah!這可以!這肯定可行!」一種安心感油然而生。雖然這樣說可能顯得過於誇張,但我確實感到被拯救了。
――這真是一個印象深刻的故事。您在進行本地化的過程中,意外碰上這樣的評價。而且我感到在此次訪談中,提到了關於翻譯的內容貌似很多,那麼關於《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的本地化,您是如何進行的呢?
SOMI: 早年在翻譯這方面,因無法妥善委託而蒙受了許多困擾。在《REPLICA》期間,我根本無法想像能以遊戲賺錢,結果翻譯品質糟糕。隨著取得人氣之後,粉絲們逐步對翻譯進行幫助。至於《LEGAL DUNGEON》,我決定尋找國內的翻譯公司來正確翻譯,但英語、日語和中文的翻譯卻比機器翻譯更糟糕,經歷了不少麻煩。
最後在《法律地牢》發佈之前,還是請粉絲幫忙翻譯。到《THE WAKE》開始,英語翻譯幾乎成為事務標準,帶動其他語言的擴展,因此我開始尋找翻譯過國內文學作品的翻譯者。而在行業中的那些擔任翻譯的多位工作者通常都非常忙碌,便無法顧及到遊戲。尋找了幾位在文學翻譯領域獲獎的人,他們也許能幫助我,因此便發送了許多個人郵件,雖大部分都因為「是遊戲」而拒絕,經過不少說服,最終遇見了現在合作的翻譯者,這也使得我的遊戲能夠將意義很好的表達出來。現在進行中的翻譯也是如此。
――在翻譯中,您特別注意哪些重點呢?
SOMI: 近來有些流行的表現,例如詩意散文。翻譯中,我常會注意如何很好的傳遞這種詩意散文。此外,翻譯與本地化這兩者之間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的本地化非常重要,故我努力進行審核。在《未解決事件是不能結束的》中,我進行了兩次審核,首次由翻譯進行檢查,第二次則不是由翻譯者,而是對遊戲及日本情緒有深入理解的人進行了再次檢查。因為遊戲中的內容氣氛乃至標題,通過不同的說法都可能改變。例如,角色的對話方式,甚至角色的名字。劇中出現的是女兒的名字,是日文的犀華,還會考慮到她的名字怎麼讀,不讓她在學校裡遭到欺負。這些議題我們不斷進行方便與討論。
因此,我與那些不會提問的翻譯者工作時,通常會處於不太合作的狀態。這個文本中的每一句話都有比喻,並且有著記號系統,也會有某種引用的原文或其他媒體能確認的東西,所以如果不常與彼此諮詢交流,很難得到一篇適合的文章。
所以在翻譯工作的過程中,我都會告訴他們「希望能多提問」。
(後編將會持續。)
